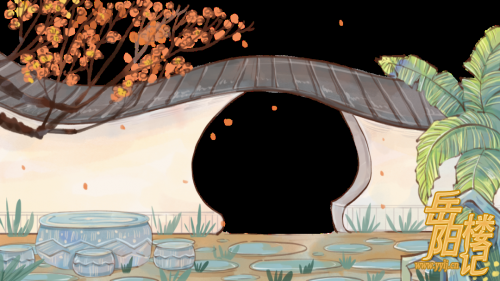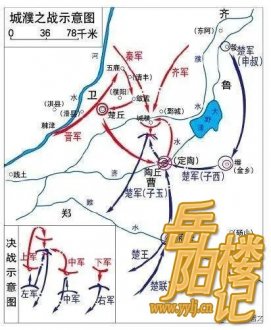《谏逐客书》:转危为安,历史意义重大
荀子在楚国,只当了兰陵小官,他的“礼”“法”思想没有得到实施,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还有武将蒙恬,身处秦统一前后,具有天然后发优势,把他的理想发扬光大,付诸实践。韩非把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政治、军事、历史复杂的、丰富的、分散的、无序的成败得失经验,进行系统化的概括,按荀子的性恶论,凝聚到政治上的法治思想。韩非感到韩日益严重的危机,几次上书韩王,不能用,乃作《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秦王看了《孤愤》《五蠹》等作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但是,历史没有给韩非施展才能的机会,但给了李斯将法治思想付诸实践的权力,对内剥夺宗族特权,对外武力兼并。不过,他的实践,也曾遇到一次重大的危机,差一点被秦始皇驱逐出境,几乎和韩非一样要留下终身遗憾了。在那狂澜既倒之时,他拼死一搏,在被逐途中,写了一篇震古铄今的文章,挽救了危机,他的法制主张乃得以付诸实践,辅佐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血腥混战,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上留下功勋。
《谏逐客书》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标题是后人所加,《昭明文选》题作《上书秦始皇》,将之归入“书”这种文体。《文心雕龙·书记》云:“战国以前,君臣同书。”臣下上书,和一般的书面交往一样称“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给帝王的书,分化为“章、表、奏、议”,一般依旧称书。书与奏议遂此分家。《谏逐客书》作于秦完全统一前,故被归入“书”。
李斯之文横跨秦汉,其前期之文,以《谏逐客书》为代表,论者以为富先秦游说论辩之风。后期则以石刻文为代表,歌功颂德,雍容大度,文简气浑。刘勰在《文心雕龙·封禅》中说:“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虽然文辞不够丰沛(弘润),但是,仍然有大一统帝国恢宏的时代风格。如泰山刻石文:“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所谓“罔不宾服”“化及无穷”“永承重戒”都是绝对化的,永恒不变的。一系列的论断都是毫无例外的,无须论辩的,而《谏逐客书》则是每一个论点都要反复论证、辩驳的。
《文心雕龙》以为“书”的功能在“尽言”,所谓“条畅以任气,优柔以释怀”,就是对朋友,对论敌,对君主,都要条理分明,理据充足,力求气壮势强。与李斯《谏逐客书》相近的如乐毅《报燕惠王书》,均以丰富的事实进行论证,语多排比。李斯的排比更加系统化。论者将其定位于上接战国纵横家之辩驳之风,下开“汉赋之先声”,此说不尽准确。严格说来,汉赋之先声乃始于《荀子》,在《荀子》中,有专门的“赋”篇,其文多重排比。李斯略减其过度铺张,其逻辑关系更加紧密,论辩色彩更浓。
从议论方法来说,《谏逐客书》可以说是先秦诸子散文论述和铺陈这两个方面的成就的总结。
事出于韩国畏秦国之威。《史记·河渠书》曰:“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据《史记·六国年表》,当时,秦穆公已经灭了梁国,惠文王灭了楚。战争非常残酷血腥。惠文王十五年击楚,斩首三万;二十二年白起击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三十五年击赵,斩首三万;四十二年白起击魏华阳君,斩首十五万;白起破赵于长平,杀卒(活埋)四十五万。正是因为这样,韩国才感到恐怖,让郑国去转移秦国的战略方向,但是用心被识破,秦宗室大臣趁机进言驱逐一切外籍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上书,终使秦王取消逐客之令,恢复其官职。郑国于面临极刑之际,陈说水利之功在富国,秦王乃使之继续领导修渠,这就是后来闻名于史的郑国渠。
《谏逐客书》虽有游说之士的巧辩之风,但是,与“说”有很大的不同,刘勰所谓“喻巧而理至”,以比喻为主,“飞文敏以济辞”,就是花言巧语。其实说得轻易,实际上问题不简单,晏子使楚,将楚这样的大国喻为狗国,居然取得成功,唐雎代表安陵这样一个小地方与秦王谈判,凭着几个现场刺客的故事,拿出“布衣之怒”比喻,做出血拼的样子,居然就把秦王吓蒙了,“长跪而谢”。好像秦王的卫士都是木头,秦王不可能当场道歉,事后追杀。这种过度夸张现场口头机智作为故事传说,作为早期小说家言则可,但是视为政治成败、自身安危之关键,则形同儿戏。故钱锺书先生引方中通《陪集》卷二《博论》下曰:
《左》《国》所载,文过其实者强半。即如苏、张之游说,范、蔡之共谈,何当时一出诸口,即成文章?而谁为记忆其字句,若此其纤悉不遗也?

这就是说,当时口头对话并非实录,而是后人转成书面时,根据想象加工,将复杂的政治军事成败归结于口才。这一点在《战国策》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本来刘向编定《战国策》有多种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刘向整合之,序曰:诸书皆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诸书颇多相互矛盾、错乱杂陈之处,刘向出于己意,斟酌取舍,增补隙漏,将之统一。不少部分为刘向之想象,但是,其中有从《左传》到《史记》之间数百年之难得之史料,乃被当成历史实录。
游说之士现场对答,当场并无记录,书者即在场亦不可能“记忆其字句”“纤悉不遗”,何况数百年辗转传抄,历史遂与传说交织,案牍纷纭,文士多慕游说之显贵,各师其心,遂将经国济世之成败,归因于现场游说。
这就透露出传播学上现场对话和书面交流的转换。
对话为现场/现时直接交流,书面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间接交流。其时书写维艰,简化保存者多为耸人听闻之巧喻,以直接线性因果构成戏剧性情节,易为美谈传说。然就历史而言,或然性,甚至无稽之谈甚多。岂不知以孔子之圣,周游列国而不得用,以孟子之贤,蓄浩然之气,不能动王侯,区区晏子、唐雎,何可比也!墨子败公输,非但以其言,且有弟子早为军备,《左传》烛之武退秦师,郑国临秦晋两大强国兵困之危,说秦退军,结盟,置晋于不顾于先,举晋之背信弃义之历史于后,战略分化敌方,化一敌为友,另一敌乃不攻自退,绝非一次现场巧喻之效。
然游说之士之现场即兴,随机应对,难能宿构,故少丰赡铺陈,乃口头传播之局限。
而《谏逐客书》,开宗明义为“书”,则非现场直接对答,全系宿构为文,字斟句酌,故其神思飞越,雄视古今,纵论八方,文采灿然,排比斐然,意气昂然。是时,李斯乃楚国上蔡人,在被逐之列。《史记·李斯列传》引《谏逐客书》后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裴骃《集解》案:“《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达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骊邑,得还。’”由是知李斯为此书,正处危难之中,观其首句: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字面上是开门见山,锋芒毕露,直接反对秦王已颁之令,但是,言词藏锋,明明是逐客之令已颁,身在被遂途中,却说是“吏议逐客”,决策尚在可议之中。直言其为“过矣”,这个“过”字很尖锐,是过错,而不是过分的意思。但是,有“过”的是臣下,明明是公开反对了,却自贬为“窃”,这当然是官话、套话,但其原意是偷偷地,也就是私下以为,降低了直接反对的强度。
李斯为书之际,危难迫在眉睫,欲使王者收回成命,复其官职。未取游说之士巧喻曲意,一来,仓促之间,形格势禁,一味兜圈子,贻误时机;二来,引喻婉曲,可能失意。其时,若用韩非之寓言故事,取庄子天马行空神话,亦可能喧宾夺主。故不能不直言,然而,一味直言可能招祸,故开头一语,字面上的锋芒指向臣下,实质是指向秦王,可谓刚柔相济。
转入正题,难点在于逐客卿有理由,反对逐客卿亦有理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共同的语言,有如聋子的对话,不能解危济急于万一。要说服其收回成命,必须找到双方都认可的理由,作为大前提。李斯的智慧在于不从抽象的道理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而这种事实是权威的,不但秦王认可,而且秦国贵族也无法反对。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这五个例子很有力度:第一,是秦国的历史,不可辩驳;第二,是先王缪公的功业,有神圣性;第三,字面上是系统的,不是孤证。结论是:用了五个“不产于秦”的外邦人,却能“并国二十,遂霸西戎”,使本来僻居一隅的,连诸侯都称不上的秦国,拓展了疆域,称霸西部中国。就一般文章而言,实证已经可以说是很充分了,对方已无反驳余地。但是,李斯所处的形势,不能以这样的论证为满足,他的目的是要秦始皇收回成命,因而论据必须超量饱和。
接下来,举孝公用卫国人商鞅变法,不但使国强民富,而且军事上战胜魏国,开疆拓土。又举秦惠文王用魏人张仪连横之计,打破了六国合纵之统一战线,三川、巴、蜀、上郡、汉中、九夷、鄢、郢、成皋之险,膏腴之地,尽入囊中。秦昭王用魏人范雎,废除了权贵,强化了王权,杜绝了贵族的不法特权,最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这样的论据,不但在质上无可辩驳,而且在量上可谓双料的饱和。
从文章来说,这样的论证颇具雄辩性:第一,所据乃以上所举之史实,没有任何游说之士所擅长的巧喻,而是像韩非一样回顾历史,系统概括秦国从落后的小国,走向统一天下的前景,皆为用客卿之功。第二,结论不仅从正面总结,而且从反面陈述,如果以拒客卿而不用,则国不克富强,疆无统一之望。
现场巧喻,即时之机智,好处在瞬间的冲击性,事后往往经不起反复推敲。而用史实,则超越现场亦不可辩驳。从形式上说,如此纷繁的例证,用排比对仗,句法结构相同,或犯重复之大忌。但是:
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

连得八捷,八句排比,皆为动宾结构,所取之地(宾语)各异,如所用之语(动词)同,则陷于单调。难得的是,李斯于此命系一发之际,居然词采纷纭,八句同构而动词各异。一则曰“并”,二则曰“收”,三则曰“取”,四则曰“包”,五则曰“制”,六则曰“据”,七则曰“割”,八则曰“散”。词异而意同,情势如此急迫,运思若此游刃有余,可窥其才之一斑。
至此论证已经相当饱和,似无以为继。但是,李斯为文之目的并非泛论客卿之功,而是要让秦始皇改变已经颁布的法令。故不能满足于在论据上作超量的倾泻。因为以上论据皆先王之功业,晓理似足,不可动摇,但是,从时间上说,有点距离,穆公生活在前七世纪,始皇在前三世纪,距离约四百年,孝公在前四世纪,距离也有约一百年,都太遥远。对于初登大位之秦王嬴政而言,欲其收回成命尚须动其情,缩短其感知距离。不但让他理解,而且让他感觉得到,看得见,摸得着。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文章的好处仍然是意同而词异,“致”“有”“垂”“服”“乘”“建”“树”,毫无重复。更突出者乃是名词,享受之物皆是最高级的,“玉”是昆山之玉,宝是“随和”之宝,珠是“明月之珠”。至于秦王的排场,所佩之剑,所乘之马,所建之旗,所树之鼓,都是举世无双的。把秦始皇置于这样空前盛大的仪仗中心,所有这一切都是秦王身体可以直接感受得到的。从现实来说,这些宝贵的物品,也许是分散的,并非聚焦于一时、一身的,但是虚拟化地集中起来,却能让秦始皇的虚荣心得到最大的满足。关键是,所有这一切回归到主题上来,都不是秦国所产,却是始皇所乐于享受的。
文章的难度在于,这么长的系列排比,似乎无以为继,再这样排比下去,难免有单调、冗长之感。李斯当然还要排比,但是,换了一种句式。前述皆肯定句式,接下来则是假定的句式,“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得出一系列否定的后果。这些后果的特点,也是秦始皇切身可以感受得到的。后果之一是:
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这一组排比已经够丰富的了,但李斯意犹未尽,又引出第二种后果:
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这一组排比与前一组排比,在结构上构成对称,形成双重排比,使得每一句不但在本系列中,而且与前系列构成有机性,每一组之增减,必然影响后一组之完整。从意义上看,这两组皆负面的后果,又反衬此前的正面效果,从意义到结构多重的内在联系,每一句都因其与之对称的句子显得不可变动,造成在思想上不可动摇的张力。
多重的排比对称强化了对“必出于秦然后可”的批驳,但是,论述到此还停留在物上,李斯的任务是把论点推进到主题上来,从物过渡到人,然又不能径情直遂,要有婉转的过渡,李斯用了音乐,虽然在结构上仍然是排比对称,但是,在意义上则进了一层,“真秦之声”遭到抛弃,代之以“异国之乐”,“若是者何也?”回答很简单,“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就是耳朵感到好听,眼睛感到好看而已。这很感性,不用讲什么道理。其实用意对双方都是不言而喻、毋庸置疑的。这个结论,比之前的论点,更进了一步,更尖锐。前面是说,用外邦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里提出,本国音乐不如外邦音乐,就自然淘汰。这已经是常识,往用人上联系达到毋庸置疑、不言而喻的效果。一般说来,正面推演,就是类比,亦应如此,但是,李斯这时用这个前提进行反推:
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文章做到这里,就不再曲曲折折,吞吞吐吐,而是图穷而匕首现,反推上一个新层次,用人不但不如物,而且不讲理。这是反驳术中的导谬法,以显而见的荒谬来证伪之后,再进一步证伪:
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反驳到了极点上,顺理成章应该是用人重于用物,这是一般的道理。但是,在李斯的思路中,这还不够,这不是一般的辩论,而是上书批评始皇。但是,直接批评的是逐客政策:“不问可否,不论曲直。”这话说得很有情感力度,但是,绵里藏针,不是从负面批评,而从正面提出:
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跨海内、制诸侯”的大志,当然是属于层次很高的人,如果不改变政策,你当然不是这个档次的人。应不应该改变逐客政策呢?不言而喻。最后,李斯则把荀子格言式的类比拿出来,类比一:
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类比二: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文势积蓄至此,可谓理直气壮了,该下结论了,但是,李斯不想让结论太简单,而是分成几个层次。先是正面:
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再是反面:
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最后把正反两面结合起来: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结论取正反合三段式,面面俱到,话说得很绝,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但是,又很有分寸,始终没有提到自己有什么愿望,却使秦始皇改变了已经颁布的决策,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文章不但比先秦游说之士的喻巧理至要理性,而且比孟子、墨子更为雄辩,其排比句法、对称的章法比荀子简明。故视之为先秦诸子散文成就的总结可能是不为过的。从思想上来说,后来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实践为李斯不拘邦国唯才是用的思想,做了充分的证明。
此文对李斯的命运来说,可谓挽狂澜于既倒,李斯复职,官至相国,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制定制度,作出了贡献。即使秦灭于汉,然汉承秦制,李斯功绩也垂于青史。可惜的是,后始皇遽亡,李斯与赵高,阴谋矫诏,令太子扶苏自尽,拥秦二世,后又为赵高所谗,于狱中欲上书,无由可达,含冤而死,当年他辞别荀子时,看准秦王有一统天下称帝之势,正是建功立业之机,当此之时,“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文学家,因才而显,因才而亡。后世读此文者,莫不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