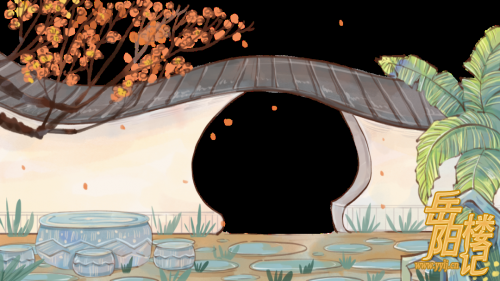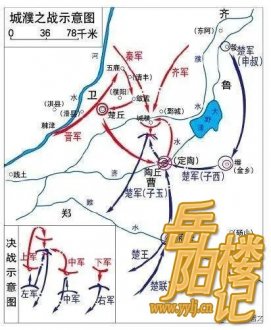统编教材课文《五石之瓠》节选自《庄子·逍遥游》,《教师教学用书》解读包括:体会“大故事”(惠子和庄子的对话)和“小故事”(“不龟手之药”的故事)的相通之处;明确这两则故事的寓意;把课文放在《逍遥游》的整体语境中把握。
[1]近有学者撰文(下称“该文”),从教材注释和《教师教学用书》对人物的褒贬中提出一个新的话题:如何评价“客”这一人物形象。
该文从分析“客”的身份、动机和品格入手,指出统编教材将“以说吴王”的“说”字注为“同‘悦’,取悦”是不恰当的,《教师教学用书》认为“客出于功利的机心”也有失允当;把从事“洴澼絖”的宋人说成“他们只能看见世俗的小利,看不到背后的‘大用’”,更属无稽之谈;至于庄子“当着惠子讲宋人的‘蠢事’,带有明显的讥讽意味”,也完全是一种误解。
[2]笔者细读该文,对其观点以及赖以得出这些观点的分析方法产生了很多疑问。
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与该文商榷,亦恭请学界同仁赐教。
一、“客”非真实且饱满的人物形象
在叙事类文本中,推动事件发展的行为主体一般被称为“人物”或“人物形象”。
广义来说,《五石之瓠》也可视为叙事类文本,说其中包含“人物形象”并无不妥。
但研究者在分析之前,往往会首先搞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这些人物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二者的分析方法有所差别。
对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譬如《鸿门宴》中的刘邦、项羽、张良、范增等,援引较可信的史料,考辨其“国别地理”“家世身份”等,帮助学生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形象特点,是完全有必要的。
对于虚构的人物,如果其国别、家世、生平之类作者并未提及,而论者非要求之于文本之外,方向上就犯了“缘木求鱼”的错误。
古今很多注家、评点家都出现过这种“以文为史”的情况。
以《红楼梦》为例,俞平伯先生说得好:《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
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其来历如何,得失如何,皆正问也。
若云宝玉何人,大观园何地,即非正问。
何则?宝玉者,小说中主角,不必实有其人;大观园者,小说中花园,不必实有其地。
即或构思结想,多少凭依,亦属前尘影事,起作者于九原,恐亦不能遽对。
[3]
第二,这些人物是“圆的人物”“扁的人物”,还是“符号化”人物?这一提法借鉴了英国小说家福斯特。
他把小说人物分为两种:“扁的人物”是按简单的意念或特性,以单纯的形式塑造出来的;“圆的人物”则性格饱满、复杂多面,不能进行简单化的概括。
[4]鲁迅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5]。
寓言作为一种文体,首要功能是说理,本不像小说那样致力于塑造人物。
但庄子极富想象,行文运笔堪夺造化之功,客观上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形象。
有学者将其简要概括为道家人物体系、儒家人物体系、百工技人形象体系、君臣形象体系、动物植物等自然界形象体系这五类。
[6]五类之中,有些屡次出现,饱满度高,复杂性强,近于小说中所谓“圆的人物”,典型的如庄子本人、“孔子”形象等。
深入研究这些形象对理解庄子思想很有必要。
绝大多数形象,如惠子、孔门弟子、隐士、神人和支离疏等“畸人”,虽然也有少量外貌、语言和动作描写,但作者只是在他们身上寄托某种观念,这些近于“扁的人物”,分析这些形象,对于从不同侧面理解庄子所说之理也有帮助。
还有个别人物,他们只是偶然出现,连姓名都没有,作者对其国别、出身、性格、心理、言语、服饰等一概略而不谈,只用其行为及结果构成情节或情节的一个部分。
这类人物只是说理的工具或符号,如果煞有介事地分析它们,难免舍本逐末、节外生枝。
观念既明,下面看看《五石之瓠》中的“客”属于哪种情况。
《庄子》全书对该“客”的叙述仅此一次,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出场: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
二是购药之后:客得之,以说吴王。
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
裂地而封之。
显然,“客”是假的人物。
如果把“客”当成真的人物,就等于把寓言当作《史记》《汉书》来读。
果真如此,“客”所说吴王是哪个吴王,诸樊、阖闾、夫差,抑或其他?吴越之战又是哪场战斗?这两个问题遍考史料无从知晓。
庄子寓言的语境是比较虚化的,需要读者去悟解。
[7]否则,文本分析必将每况愈下,甚至有可能沦落到讨论:“实五石”的“大瓠”究竟是怎么种植、培育出来的?更明显的是,“客”是符号化的,非但不是“圆的人物”,连“扁的”都不算。
譬如俗谚“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里固然是有人物在的——“三个和尚”,但我们只要观其大略,知道是在讽刺因互相推诿而自食其果的现象也就够了。
非要引申开去,说第一个和尚本来勤劳、善良,有自力更生的性格;第二个和尚的到来使他产生了“分工”意识,凸显了他的智慧;第三个和尚的到来使大家对分工方法产生了困惑,以致喝不到水,故值得同情云云——虽不能说是“无稽”,总未免有些“滑稽”。
申丹老师对此做过精辟论述:“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
“心理性”人物观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人”,而不是“功能”。
对于某些以人物塑造为主的心理小说,“功能性”的分析方法难以施展;而对于某些以事件为中心的程式化的作品,“心理性”的分析方法也意义不大。
只有在将人物与事件有机结合的作品中,这两种分析方法的互补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就我国的批评实践来说,认清这两种人物观的适用性、局限性和互补关系有助于避免分析中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8]显见,基于“功能性”人物观来分析“客”这类人物是更为合适的。
二、该文对“客”的分析误区及其澄清
该文综合古代文献,概括得出“客”具有三方面特点:①客本吴人,吴越战事熟谙于心;②既得方术,游说吴王成竹在胸;③智勇双全,冬月水战大获全胜。
进而根据这些推论为“客”鸣不平,认为教材注释和《教师教学用书》使“原本胸有谋略、坚毅果敢的君子形象,一下子跌落而成为趋附逢迎、巴结讨好的小人”。
恕笔者直言,这些分析和评判实在是“用错了力气”“表错了情”。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庄子研究还是语文界庄子教学研究,从没有一位学者这样分析过“客”的形象,连综述《庄子》形象体系这类文章都对这个“客”只字未提。
何哉?因为他是无可稽考的假的人物,同时也是毫无“心灵史”可言的符号化人物,没有家世、心理和性格分析的必要。
就庄子来说,他对“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本是当成“蜩与学鸠”来看的,怎么可能着意塑造“胸有谋略、坚毅果敢的君子形象”?该文之所以大费周章,除文本分析方向不明、人物形象定性不准外,具体方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使用古代文献应加甄别。
该文引《太平御览·时序部十二》和《五先堂文市榷酤》卷四《拘挛篇》,试图说明古时有人直称“客”是吴人,从而为自己“客本吴人”的观点张本。
至于这些文献凭什么说“客”是吴人,该文说“当系依据情理因素分析推断而得出”,那又是什么“情理因素”呢?文献本身没有给出解释。
对于这种文献,理应追问古人所言是否臆断,他们的分析方向和方法有没有问题,而不是直接采信。
再如,该文引成玄英疏,用以证明“客”具有优良品质。
成疏是针对“客”购药后的文字做的,原文是:“吴越比邻,地带江海,兵戈相接,必用舻舡,战士隆冬,手多拘坼。
而客素禀雄才,天生睿智,既得方术,遂说吴王。
越国兵难侵吴,吴王使为将帅,赖此名药,而兵手不拘坼,旌旗才举,越人乱辙。
获此大捷,献凯而旋。
勋庸克著,胙之茆土。
”“疏”是对“注”的进一步解释,包括介绍背景、解释字词、疏通文意、阐明义理等,本意在于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但很多时候,注疏之人对原文的理解未必准确,或者有意无意发点感慨,这些内容往往会误导读者。
成疏整体质量很高,例如,在“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句下疏云:“斯盖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实乎!宜忘言以寻其所况。
”[9]历代学者都认为这是读《庄子》的正道。
但有时成疏的“代入感”过于强烈,不但不能“忘言”,还要借题发挥。
例如对“客”的这条疏文,字下加点(按:加粗)的句子是对事件背景的介绍,是应有之义。
未加标记的字句是对原文的串讲,补充了一些因果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画线字句则纯属成氏的想象:“素禀雄才,天生睿智”是想象其素质,“旌旗才举,越人乱辙”是想象其战斗,“献凯而旋”是想象其归国。
在这一刹那,成氏顾不得庄子的写作目的和写作重点,他沉浸在阅读传奇、小说似的情绪中了。
我们不能苛责古人对阅读思维的自我监控不够,毕竟当时的阅读理论还远不完善,但时至今日仍亦步亦趋,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第二,应区别作家和评论家所肩负的责任。
该文在论证“既得方术,游说吴王成竹在胸”时强调:“虽说‘客’的这些特点在文中都略而不书,然而根据现有描写还是能据理分析还原,使人物形象更加充实饱满。
”须知,使人物形象充实和饱满,是作家的职分,不是评论家的责任,用庄子的话讲就是“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换言之,评论家分析文本,应该关注“哪个人物充实和饱满”“何以充实和饱满”等鉴赏方面的问题。
倘有“越俎代庖”的心力,也应该像金圣叹一样,既以“第一读者”的身份评点之,又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削删之,[10]而非沉湎想象,于文外添枝加叶。
况且,叙事类作品并不是所有人物都是“圆的”才好,其他类型也不可或缺。
以庄子的笔力,他“略而不书”,一定有“略而不书”的原因,譬如虚化人物,聚焦事件,更好地为说理服务,等等,这才是评论家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第三,要注重对自我的“前经验”的反思。
文本分析过程中,分析者会不经意地受到原有观念的左右,并以此为前提得出推论。
如果这些潜在观念本身经不起推敲,推论自然无法成立。
该文在论证“客本吴人”时,似乎也感到所引文献没有讲明“情理因素”,就自己做了补充:“若换成别国之人,既不了解吴、越之间水上交战的细节因素,又缺乏重金购买药方之迫切想法和动力,要做出‘请买其方百金’的行为是缺乏现实可能性的”。
这一观点的“前经验”是:①只有吴(越)之人才了解水上交战的细节因素;②只有吴国人才有为吴国效力的动机。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士”的阶层是异常活跃的。
他们游走列国诸侯之间,以建功立业为己任,未必都像弦高那样报效母国。
同时,为显身扬名计,他们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民生都有很深的了解。
且不说战国后期以合纵连横之术操控天下的苏秦、张仪,即使是早于庄周的伍子胥,本身也是楚人,为报父兄之仇才投奔吴王阖闾。
伍子胥主持营建姑苏城,率水陆之兵攻破郢都,他会连冬天水战皮肤龟裂的常识都不知道吗?再如,该文认为,若把“说”字解读成“取悦”,会使“客”一下子跌落成为趋附逢迎、巴结讨好的小人,其“前经验”是:取悦君王就是小人,这就未免把人类的道德底线定得太高了。
“取悦”是“讨取别人欢心”的意思,看起来的确不够耿直,但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又不能一概而论。
其中固然有易牙、李林甫等动机不纯的真小人,也不乏傥傥大节的君子为做成有益于国民的事业而逢迎君主。
如果说“取悦君王”就能使人物形象一落千丈,则中国历史上除屈原、魏征等极少数外,君子还有几人?
三、“客”说吴王是出于“功利的机心”
既然“客”是符号化的人物,应据“功能性”人物观加以分析,为何《教师教学用书》还要说“客”是出于“功利的机心”?是否果真如该文揣度的,是《教师教学用书》的作者“自身带着功利的眼光去赋予文献中人物的褒贬评说”,或者因为庄子一句“或以封”,就以客观结果来推断其主观动机?对此,不妨先看看《教师教学用书》原文:
庄子以超凡的智慧说出大葫芦的“妙用”,在境界上与吴王之客是相似的。
这是“小故事”对“大故事”的第二个作用:凸显庄子的超拔。
需要说明的是,吴王之客眼光再高,也仅仅是功利的心机,而庄子“浮乎江湖”的想象,则隐含精神的自由,二者不是具体做法和价值取向上相似,只能说在“宋人与客”和“惠子和庄子”这两组对比关系中体现出的境界高下相似。
很明显,《教师教学用书》是在对比的语境中说的:说“客”功利是宾,衬托庄子境界是主,目的无非是通过“宋人与客”和“惠子和庄子”两则故事的内部比较和“跨故事”比较,帮助师生深入理解课文。
所谓“功利的机心”,一般指出于利己的目的行事。
该文认为,如果“客”的动机是为自己国家助一臂之力,就不能说是功利的,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层。
[11]依该文主张,“客”应在道德境界。
但如前所述,包括成疏在内,对客的真实动机的推断都属于脱离文本的臆造。
换言之,《教师教学用书》证明不了客的动机一定是谋求爵禄,该文和成疏也证明不了客的动机一定是报效母国。
但站在“功能性”人物观的立场,基于东周士人的一般价值观,比照列国才智之士的普遍动机,说“客”处在功利境界而非道德境界,明显更符合寓言背后的社会历史环境。
退一步讲,即使把“客”包装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爱国志士,这些“人间世”的所谓“道德”,放在追求“逍遥游”的庄子面前,说一句“道德即功利”,也未为不当。
关于教材注释,以笔者愚见,解释为“游说”或“取悦”都说得通。
诚如该文考辨,“说”字两义都有,且均常用。
但是,凡“游说”“说服”,“说”者向被“说”者所进多为“言辞”。
言辞有理,可使被“说”者改变观念,依从说客之言决策、行事,如“触龙说赵太后”“范雎说秦王”“苏秦以连横说秦”等。
而在《五石之瓠》中,“客”向吴王所献者为“物”(药方),也并非希望吴王接受某种观念或者改变原来某种行为,称其“取悦”似更合理。
该文担心此注有损“客”的人格,如前一节所述,是多虑了的,况且“客”作为符号化的人物,压根儿谈不上人格问题。
另外,该文列举多个版本,注释均与教材不同,但这些不能直接证明教材注释有误。
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谈到词义注释与文意注释的区别时,举过李白《春思》的例子:“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清代章燮注:“低,叶盛貌。
”“低”没有“繁盛”的意思,但“树枝被压低,是叶和果实盛多的缘故,‘低’是具体的形象,‘盛’是低枝的原因,这也是对言语意义的解释”。
这种文意注释“是中国古代训诂的一种惯例”。
[12]由是观之,“说”字非但本有“取悦”之意,亦能与课文语境贴合,当成文意注释来看无可厚非。
四、庄子对“洴澼絖”的宋人持有褒贬态度
文本分析不仅要重视古代文献的梳理,也要关注当代学者的研究。
《教师教学用书》虽未像该文所说的那样对“洴澼絖”的宋人“极尽贬损之辞”,但确实将其所作所为评为“蠢事”,并且指出“蠢”的原因是“只能看见世俗的小利,看不到背后的‘大用’”,还强调“客的眼光和做法超过宋人太多”。
该文说这些是“新的解读”,并指为“无稽之谈”,正是对当代庄子研究关注不够所致。
庄子研究界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学者大有人在,姑举两例。
“贬损”色彩较浓的如杨义先生,他不止一次提到“洴澼絖”的宋人:①宋国漂絮者有不龟(皲)手的祖传妙药,只能世世漂絮,而别人用此药于吴越冬日水战,却可裂土封爵,此类宋人愚拙故事,是由于庄氏家族流亡后未能融入宋国的缘故。
[13]②宋国有个家族,发明了一种使手不皲裂的药膏……有个客人想用百金买他们的药方,他们就开家族会议讨论……那位客人……受到吴王的裂土封爵。
而宋国这班老兄,还在那里洗他的破棉絮。
宋人封闭狭隘,使他们只看到一点儿蝇头小利,不懂得如何使自己的专利权发挥更大的作用。
[14]“贬损”色彩较淡的,如暨南大学宋小克认为:庄子所谓“愚人”,多因“小知”遮蔽“大知”……宋人知道出售“专利权”,不属于抱残守旧者;知道衡量“数金”与“百金”的利害,做事也理智冷静。
宋人之智仅限于此,精于计算,而对不龟手之药的“大用”茫然不知。
[15]
其实不必过多引述,《逍遥游》原文就写得明明白白。
首先,庄子讲宋人故事时特意加了一句:“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
’”“聚族而谋”就“谋”出这么个结论来,庄子的“贬损”态度显而易见。
该文在介绍故事内容时,却偏偏把这段话省略了。
其次,《庄子》寓言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有内在理路。
把《五石之瓠》放在《逍遥游》中全篇考察,对“洴澼絖”的宋人和对惠子的“贬损”是沿着“小大之辩”一脉贯通下来的。
“大鹏积厚图南的高远心志,却引来俗世中自得于一方之人的讥笑,因而庄子补充一段蜩与学鸠的寓言,说明在人生的历程中,长途跋涉者,需有丰厚的聚粮,而蜩与学鸠根本无法理解小角落之外的大天地,故而庄子评论说:‘之二虫又何知。
’”[16]吴怡从辨“小”“大”入手,指出庄子的“大”并非在形体上、财物上、势位上比别人多的“大”,庄子的“大”就在于他的精神境界。
关于“小”之形成,括而言之在于两端:一端是受拘于经验;另一端是执着于偏见。
[17]“洴澼絖”的宋人虽然没有嘲笑“大”,但他毕竟拘执于经验,评之为“蠢”“愚拙”或“狭隘”,不亦宜乎?
该文所谓“地处北方的宋国人,不存在类似南方吴、越两国的水上交战之事,将‘不龟手之药’用于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洴澼絖’,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便所得报酬微薄,但能坚持以世代相传的这一技术服务于社会,至少从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念上来说是不该被贬低的”,这就等于把宋人故事硬生生地从文本的语境中“拖拽”出来,用今人的眼光作出静态、孤立的评价。
至于该文认为庄子列举“客”凭借药物“裂地而封”和宋人虽有药物而不免于洴澼絖的两种现象,并没有褒客而贬宋人之意,而是表明物之用以各得其所或各有所当为评判标准,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庄子“没有褒客而贬宋人之意”,该文用数千字给“客”树碑立传,所为何来?难道在同一篇论文之中,为驳教材注释就可以用“合理推断”去美化“客”,为驳《教师教学用书》对宋人的评价就可以说庄子两无褒贬?
究其根源,还是受了文献的“蛊惑”。
该文引用了很多古代文献,但一方面缺乏甄别,另一方面没有厘清文献之间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逻辑关系,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拿来就用,不利的则视而不见。
例如,该文综述古人对“所用之异”的解释,前两种即“用之工拙”与“用之大小”,基本符合庄子原意,但因为不合作者之意,讨论时就只用了后两种,即“用适其材”与“用之得宜”。
而主张“用适其材”的王雱(王安石之子)在这个注释上不过是承袭郭象的观点。
那么,郭象注《庄子》都是在阐发庄子的原意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刘笑敢先生早就做过深刻揭示:①《逍遥游》原文歌颂鲲鹏的远大宏图、悲悯“二虫”无知无识之意十分明确。
这里的“二虫”指前文所说主语之蜩与学鸠,上下文毫无误会的空间。
但是,郭象注释却说“二虫,谓鹏、蜩也。
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
……此逍遥之大意。
”这里明目张胆地将“蜩与学鸠”改换为鲲鹏与蜩而遗弃学鸠,从而抹杀鲲鹏与“蜩与学鸠”的大小不同。
这究竟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窜改?“鹏”与“学鸠”之字形、字数都不同,疏忽误读的可能性应该不高。
如果确是误读,那说明郭象阅读原文异常草率。
如果不是误读,则是郭象有意为抹杀原文小大之辩而为之。
②郭象在《逍遥游》题注中所说的:“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笔者注:此句亦为该文立论之本)此说作为全书开篇题注先声夺人,将《庄子·逍遥游》原文的“小大之辩”的主题转换为郭象自己的“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的观点,即大小为一的观点。
熟悉《庄子》一书的读者都会想到,郭象实际上是在挪用《齐物论》中大小为一的观点来扭转、抹杀《逍遥游》中的大小之辩。
[18]
该文把郭注当成了庄子本意,因此得出了庄子“没有褒客而贬宋人之意”以及所谓“真正寓意”等一系列推论。
而《教师教学用书》“贬损”宋人以及对故事寓意的阐发——“‘小故事’的寓意可以理解为:同一种事物,用法不同,价值就不同。
因此要善于转换视角,发现和发挥事物的最大价值。
在‘大故事’中,庄子运用了‘小故事’中蕴含的方法论,借如何处置‘五石之瓠’,说明了‘无用之用’才是‘大用’的道家哲学”,则是对古今学术文献梳理、考辨之后所做的“教学转化”,所论者乃庄子之文,而非郭象之注。
另外,该文非议的“发现和发挥最大价值”等语句,也不是什么“无稽之谈”。
王富仁认为,庄子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过往人们对瓠的实用价值的认识上,而能够带着这个“瓠”在整个宇宙间自由地游弋,并且在江湖之上为这个“瓠”找到了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空间,亦即发现了它的新的、更加巨大的实用价值。
在这里,庄子揭示的实际是人类认识与人类精神自由的关系的问题。
[19]而《教师教学用书》未对来历详加解说,盖因写给一线教师参考的工具书,明白晓畅为宜。
五、庄子对惠子讲宋人故事极可能带有讥讽意味
该文认为“当着惠子讲宋人的‘蠢事’,带有明显的讥讽意味”是一种误解,其逻辑可能是:既然宋人所为不是“蠢事”,也就谈不上对同为宋人的惠子的讥讽了。
这一点上节已明,仅补充两点:
第一,“愚宋”现象在诸子中普遍存在。
杨树达先生1926年曾作《说晚周诸子中之宋人》一文,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
他列举了《孟子》的“揠苗助长”、《韩非子》的“守株待兔”、《淮南子》的“教子私藏”等“愚宋”故事,提出“按宋人不尽愚,何以天地间至愚可笑之事皆属于宋人耶?此必有其故矣”。
后来多有学者补充和阐释,如王永《先秦“愚宋”现象与〈汉书·地理志〉之地域文化观》、杨义《先秦诸子发生学》等等——这类文章大多把“不龟手之药”作为“愚宋”故事的典型。
第二,据杨义先生考证,庄子虽是宋地蒙人,但祖脉在楚,其家族为楚庄王后代,大致在楚悼王或肃王时,成为疏远贵族。
作为楚国流亡公族苗裔,庄子并未融入宋国的贵族政治,在精神和心理上“常作楚思”,而宋人在其笔下则多呈“朴拙之相”。
[20]这就解释了庄子何以身为宋人居然仍能“了无挂碍”地“愚宋”的原因。
有了这两点,再看《五石之瓠》原文,不难发现:惠子以“五石之瓠”发问,实际是对庄子思想的发难,庄子“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则是对其直接的回击,这是二人论辩的大语境。
在这个大语境下,庄子明知对方是宋人,开口就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的“愚宋”故事,放在交际情境中判断,极可能带有讥讽的意味。
当然,《教师教学用书》说“带有明显的讥讽”是有些武断的,加上“极可能”,则更为严谨。
总而言之,文本分析是教学设计与实施的基础,也是用好教材的前提。
这一工作看似简单,实则要求分析者参与到与作者、与文本、与文献、与自我、与敌论者的多向度对话中。
这些对话活动在文本分析实践中总是错综复杂地交织,且因文本特点的不同而千变万化,这就要求分析者灵活运用适应不同对话对象的分析方法。
唯其如此,才能得出具有语文学习价值的阐释与评价。
[本文系教育部教材建设研究重点规划项目“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基础选篇研究”(项目编号2021-GH-ZD-JJ-Y-02)成果。
]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用书·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55.
[2]陈明洁.浅议《五石之瓠》中“客”的人物形象[J].语文学习,2021(7):63-67.
[3]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6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435-436.
[4]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8-59.
[5]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5.
[6]张洪兴.《庄子》形象体系论[J].船山学刊,2010(1):102-104.
[7]王锺陵.略论庄子表述的三种方法:寓言、比喻、类比[J].文学遗产,2009(2):4.
[8]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2-61.
[9]郭象注,成玄英疏,黄础基、黄兰发点校.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15.
[10]陈才训.论评点者对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36-144.
[1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497.
[12]王宁.语文教学与提高语言运用能力[J].中学语文教学,2005(8):58-61.
[13]杨义.《庄子》还原[J].文学评论,2009(2):7.
[14]杨义.先秦诸子发生学[J].文史哲,2014(4):12.
[15]宋小克.宋国愚人及其文学演绎[J].中国文化研究,2013(2):97-98.
[16]陈鼓应.《庄子》内篇的心学(上)——开放的心灵与审美的心境[J].哲学研究,2009(2):28.
[17]吴怡.中国哲学发展史[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171-172.
[18]刘笑敢.从超越逍遥到足性逍遥之转化──兼论郭象《庄子注》之诠释方法[J].中国哲学史,2006(3):5-14.
[19]王富仁.论庄子的自由观——庄子《逍遥游》的哲学阐释[J].河北学刊,2009(6):45.
[20]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