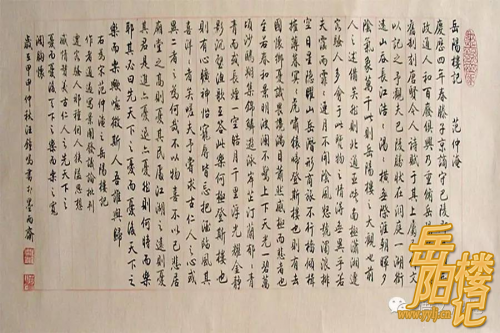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应好友滕子京之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名动天下的《岳阳楼记》,亦因此得以应运而生。数千年以来,治国平天下一直是读书人终生为之奋斗追求的目标,然而第一次,有人以一种直抒胸臆的方式,于天地间发出如此响彻千古之声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故此文甫一面世,无论当世之人,还是后世之人,少有不为文正公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而折服、倾倒。


曲初奏谐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此是文正公开笔第一句。倘是对宋史,尤其是“庆历新政”有所了解的人,当知道,与“庆历四年春”和“谪守”两词产生联系的又岂止是滕子京一人之命运。
庆历三年,是范仲淹经历半生仕途沉浮后,终掌中枢大权的一年,亦是为庆历新政唱响奏曲的一年。宰相是其视之如父的杜衍,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相),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富弼二人,则与他志气相投;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4位谏官,亦皆是知己之交。天时、地利、人和,一时俱全。故素有整顿吏治、加强武备、改善经济之志向的范仲淹,于此年夏天,在宋仁宗责令条陈政事之际,当庭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借此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
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由此拉开了序幕。
庆历三年秋,新政开始渐次向全国颁布推广。倘无意外,来年的春天,将是新政在全国上下全面开花的大好局面。可以这样说,庆历四年春,这应是一个被范仲淹寄寓了无数美好期待的春天,如同大自然的生机勃发、繁花似锦,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在经历了数十年苦寒、风雨之考验后,亦似乎终于可以在这一个春天里尽情绽放了。

戛然而止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未及盛开,便以一种凄然、壮然而又惶然的方式凋零了。甚至有点不堪的意味在里面。
以夏竦为首的政敌们,利用诽谤和构陷之手段,对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韩琦、富弼、杜衍、欧阳修等人,就士大夫安身立命最为基本,亦最为重视的两个方面——政治大节和私德品行,报以种种恶意攻击和抹黑。在政治大节方面,他们就“结党”一事大做文章,而范仲淹在面圣自辩时,因自认坦荡,问心无愧,反而就势提出了“君子党”之一说。欧阳修则更猛,他直接撰写了一篇言辞激烈、文理并具的雄文上呈仁宗皇帝,题目就叫《朋党论》。可惜的是,文章是好文章,殊不知,已然犯了一个天大的忌讳。诚譬如一个医者,任其制药的本领再高,若不擅把脉,所开之药不但不能对症,反倒成为害命之药了。
所以,关键的问题出现了。欧阳修也好,范仲淹也好,这哥俩谁也不曾摸清楚仁宗的“脉”,抑或说,他俩皆不曾真正看透赵宋王朝君主们“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之下,那份根植于骨子里的隐秘防备之心理。
宋之“重文轻武”,乃是太祖立国之初便制定的国策。且终两宋300多年的王朝统治,赵宋的后嗣君主们或许有各种毛病,但他们大多皆能恪守宋太祖遗训。同样是勒石为戒,偏安一隅的南宋君主,在国破碑失后,震慑犹在;而明朝倒好,直接让一个叫王振的太监将铁碑搬走砸坏了。
然宋太祖自己本是武将出身,却为何如此“重文教,轻武事”呢?概因宋的江山,并非凭着强大的实力打下来的,而是肇始于一个偶然的事件:黄袍加身。这在整个历史上,亦是不多见的。导致这个现象的,恰恰是源于晚唐的藩镇制度。藩镇割据,发展到后期,就是谁的拳头厉害,谁就是老大。诚如后晋将领安重荣所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所以亲信取主上而代之的事件,在短短几十年间,时有发生。五代十国就如一幕幕历史短剧,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里,再无秩序与道义可言,背叛与杀戮取代了忠诚与仁慈,强大的武力就是规则。
陈桥兵变,亦不过是藩镇制度的一个缩影而已,或者说是一种升级版的僭越行为罢了。虽然,赵宋王朝亦因此而来,却诚不愿,日后或有人效仿之。
善于总结的宋太祖还发现,强大如唐帝国者,除了藩镇制度使其中央集权失控外,中晚唐之失,亦在于党争为祸甚烈。所以,警惕官员结党,犹是成为宋太祖及其后嗣君主们之共识。
是故,当仁宗皇帝一听到结党之词,这位素有仁爱之名的帝王亦不免敏感起来,再加上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振振有辞,更使他忌惮不已。即便早先的仁宗,对新政确实抱有极大期待,然在此时,亦不得不有所动摇了。

卷入党争

可见,在揣测圣意方面,他们的政敌,显然更加技高一筹。当然,或许在范仲淹这样的磊落君子看来,大丈夫既以天下为公,又何须揣测圣意?然而,在一家一姓之天下的时代,失去圣心,这一仗,亦意味着他们已呈必输之局面了。奸险如夏竦者,为使宋仁宗彻底厌弃范仲淹等人,紧接着又出了一个大招。史载,他令家中使女天天临摹太子中允石介的笔迹,等足可以假乱真时,便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其中有一段话,最是致命,即劝说富弼效尹霍二人,行废立之举。此伪密信之一出,纵范仲淹与富弼之忠心天地可鉴,文章如何了得,亦是白沙在涅,再无法自辩清白了。
至此,两人只能借边事再起,分别于庆历四年的八月、九月,自请出京巡守了。
历朝历代,凡推行新政与改革,纵于国于民有利,然对既得利益者而言,却是大大不利的,故往往群起而攻之。而范仲淹新政中的“抑侥幸”,其刀锋之所指,就是权贵子弟的荫恩机会。这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任何调和之余地。史载,范仲淹为相,锐意改革吏治,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一笔勾去。枢密使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宋人爱以“丈”称呼尊长,这里的十二,当是指范仲淹在家族同辈中的排序。这里的枢密使,乃是富弼。富弼亦非怕事之人。宋史记载,他多次出使辽国,且每次皆据理力争,坚决不肯割地。由此即可看出,这绝对是一位颇具胆识的人。而他所以在一旁说话,只是让范仲淹有心理准备,这每一笔下去,对所涉及之人及其家族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击和报复。
而范仲淹的回复,亦正贯彻了他一直以来的凛然之气节:对不称职者的“残酷”,正是为了对更多苍生负责。
然而,面对范仲淹们的“不容情”,夏竦们的反击也来得更加猛烈与恶毒。
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富弼亦于同日被罢去枢密副使。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三月初,韩琦亦被罢去枢密副使。
然夏竦犹未罢休。在私德品行上,他则攻击欧阳修与名分上的外甥女张氏(其妹夫前妻之女)有私情,且借欧阳修早年所作的一首词,大做文章。欧阳修百口莫辩,虽事后查无实据,但终究名声有碍。于庆历五年八月,亦黯然离京,去了滁州做太守,其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亦是作于此期间。
随着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与欧阳修等人一一被逐出朝堂,庆历新政自然也随之“流产”了。

热眼旁观

然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庆历新政自发起,到以一种狼狈不堪的方式落幕,我相信,有一个人,始终在默默而又冷静地旁观着、思考着。亦正是此人,在范仲淹死后,其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推崇之情,跃然纸上。他,就是有宋一代,掀起最大变法风暴的改革猛将,亦是列宁口中的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时为庆历二年的新晋进士王安石。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于大宋朝而言,这是一场既是前所未有的,亦是绝后的改革。其无论从规模、声势,还是深度与力度上,皆是之前的庆历新政所无法比拟的。后者所引发的争议之广泛,影响之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王安石亦因变法,而背负了数百年的骂名,以至于《宋史》之“奸臣传”中,亦有其之耻辱一席。
此诚不公也。倘一个人,其思想超前于同辈之人5至10年,世人当以奇才视之;及至几十年,亦必然有人奉其为神明。然若是一个人之观念,超前了数百年乃至千年,所有人只会将其“妖魔化”,故王安石之罪,不在于其人如何,而在于其经济理念实在太超前了。
原因很简单,一个接近于近代的财税制度观念,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封建体制国家里,注定是难以实施的。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经济思想,亦是他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们争论不休的焦点。王安石认为,社会财富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定数,而是可以通过价值的再创造实现更多。但司马光等人却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言即天下的财富是定量的,国用增加了,就意味着夺民之利了。
司马光是一位读四书五经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亦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然而,他在史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光辉,亦掩盖不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短板。他有着士大夫所能够具备的一切高贵品质,忠君爱民、刚正不阿。因为觉得王安石的变法会“夺民之利”,所以,作为好友的他,不惜与王安石反目成仇。甚至,多年后他为副相时,新法亦最终在他手里,被毁于一旦。
命运就是如此荒谬且悲凉,反对力量最为集中,亦最为猛烈的,几乎全是来自与王安石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故旧亲朋那里。其中,既有王安石变法的前驱者——昔日“庆历新政”的主将们,如三朝宰相的韩琦、富弼,以及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亦有与王安石相交莫逆的好友,如反对派中的司马光、吕公著、韩维三人,还曾与王安石有“嘉祐四友”之称。可以说,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大臣,分明是代表了那个时代最为精英的一个士大夫集体。
范仲淹的“庆历四年春”,以无尽的遗憾,在历史上留下了悲凉的一页。他永不会想到,25年后,同样一个春天,同样是参知政事,同样壮怀激烈、忧国忧民,同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同样是以失败而告终,但个人的结局却又如此不同。范仲淹仅凭“文正”之谥号,则足见其不论生前身后,名声无碍。而王安石,却远没有他的这份幸运。
这是大宋的悲哀,是王安石的悲哀,亦是历史的悲哀。
除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几乎是孤军作战。他破格提拔的一些年轻人,除了让他日后在史书上平添一笔令人诟病的话题外,并未能发挥多少实质性之助力。然而,王安石何许人也,人称“拗相公”的他,又岂会轻言认输,何况,他亦坚信,“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此当是解决宋朝积贫之唯一出路。故王安石亦是“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也”。
王安石如此,司马光等人亦如此。这是由宋神宗一朝所开启的一个独特之政治现象,它打破了中国古代政治向来非黑即白的定律,即朝堂上的对立,正派与反派一定是极为分明的,在宋代中期的朝堂上,谁都代表了正义,谁也都不全然无辜。起初,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认定的“正义”而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相争到最后,这份“正义”亦失去了最初的味道,逐渐演变成纯粹的新党与旧党之争,这就让人始料未及了。
事实证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何其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