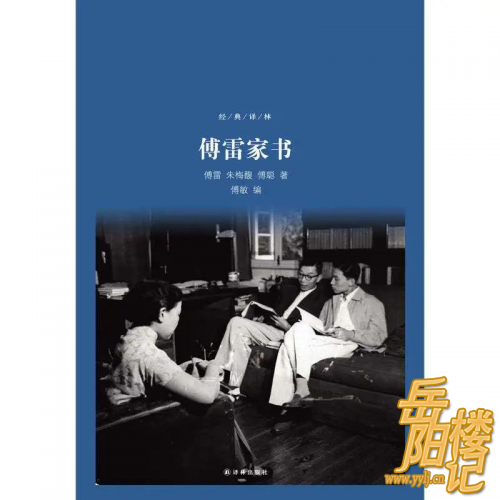《孔乙己》中的“我”是咸亨酒店里的小伙计,也就是说,作者有意地选用“小伙计”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这个事实是人们在读《孔乙己》这篇小说时,很容易就注意到的。
但却很少有人进一步深究:作者的这一“叙述者”的选择后面的“意味”。
叶圣陶先生在《揣摩——读〈孔乙己〉》(1959年作,文收《叶圣陶集》第10卷)里曾经说到这个问题。
他指出:“用第一人称写法说孔乙己,篇中的‘我’就是鲁迅自己,这样写未尝不可以,但是写成的小说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跟咱们读到的《孔乙己》不一样。
大概鲁迅要用最简要的方法,把孔乙己的活动的范围限制在酒店里,只从孔乙己到酒店喝酒这件事上表现孔乙己。
那么,能在篇中充当‘我’的唯有在场的人,在场的人有孔乙己,有掌柜,有其他酒客,都可以充当篇中的‘我’,但是都不合鲁迅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是被观察被描写的对象。
对于这些对象,须有一个观察他们的人,可以假托一个在场的小伙计,让他来说孔乙己的故事。
”
应该说,叶圣陶先生的这一分析已经相当中肯。
我们就在此基础上,稍作一点申说与展开吧。
按叶老的分析,鲁迅原可以有四种选择:“孔乙己”“掌柜、酒客”“小伙计”与作者自己,都可以充当故事的叙述者“我”。
现在,我们就用“排除法”来逐一讨论鲁迅为什么“不”那样选,这与他的追求(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有什么关系。
首先,鲁迅没有选择“孔乙己”自己作故事的“叙述者”。
这涉及鲁迅所特有的观察(世事与人)方式与艺术构思特点:鲁迅从来不孤立地观察、描写“人”,而是把“人”置于与他人(社会)的“关系”(首先是“思想关系”)中来观察与表现。
鲁迅在具体考察、描写中国社会时,他有一个重大的艺术发现:在中国,不仅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吃人”,而且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所形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更在无时无刻地制造着“吃人”的悲剧;这在鲁迅看来,后者是更为普遍,更不露痕迹,因而是更为可怕的。
因此,他总是要在他的悲剧主人公的周围,设置一群“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构成一种社会环境、氛围,或者说,把他的主人公置于“社会”(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中,在与“社会”(群众)的“关系”中来展现他的悲剧性格与命运,从而形成“看/被看”的叙述模式。
这样艺术构思就决定了鲁迅不可能选择孔乙己自己作“叙述者”,那将是一个单一的视点与视角,是鲁迅所不取的;而必得从孔乙己周围的人中选取一人来作为叙述者,从而形成两个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视点与视角,这就是小说所一再描写、反复渲染的孔乙己的自我审视、主观评价与“周围的人”(社会群众)对他的观察、评价的巨大反差。
比如,在孔乙己的自我感觉里,他是“清白”而高人一等的,但在周围的人(社会、群众、看客)的眼里,他却是“好喝懒做”、没有任何地位,任何人都可以欺辱(重则将其打得半死,轻则将他取笑)的;在孔乙己的自我评价中,他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他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这类特殊价值是芸芸众生不可望其项背,也无法理解的,但在小伙计的视角里,“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除了成为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之外,孔乙己已无任何价值可言。
因此,到小说结尾,人们之所以还提起他,仅仅因为粉板上记载着他“还欠十九个钱”,待到粉板上将他名字涂去,人们就将他完全忘却,以至于他的“结局”,人们只能说“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是“大约”死了还是“的确”死了,已无人弄得清楚,更无人过问、关心了。
这样,作者就通过双重视点的巨大反差,不仅写出了孔乙己个人的悲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吞噬”的悲剧,而且它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和社会上大多数人对知识分子的观察与评价(它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之间的对立和反差,超越时空,具有更大的概括性与普遍性。
尽管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做着“王者师”的美梦,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正如鲁迅所说,皇帝老子只有在开国(交好运)与亡国(倒霉)时才想起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不过是充当“帮闲”与“帮忙”。
时至今日,知识者的自我评价(自我立志)与社会实际地位的反差,还依然存在,甚至有日益增大的趋势。
这种反差所显示的知识分子地位、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岂只“孔乙己”一人而已,岂只“孔乙己”那个时代而已。
那么,作者为什么不选择“掌柜、酒客”作为“叙述者”,直接用这些“看客”的眼光去“看”孔乙己,不是可以更强烈地显示出孔乙己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吗?这同样也涉及鲁迅对社会关注与艺术构思的基本特点:在鲁迅看来,在中国这个一切都“戏剧化”“游戏化”的国度里,“人”不是充当“看客”,就是“被人看”,这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因此,鲁迅的关注从来都是双重的,把“被看”者与“看客”同时纳入他的艺术视野,作为他的“被观察被描写的对象”。
从这样的创作意图出发,“小伙计”正是再恰当不过的“叙述者”(观察点):一方面,他是酒店中人,“孔乙己”(被看者)与“酒客、掌柜”(看客)这两类人的一言一行都“尽收眼底”;另一方面,他的地位与身份决定了他不仅与“孔乙己”,而且与“酒客、掌柜”都有一定距离,他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讲述(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掌柜)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看”“被看/看”的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中同时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
另一方面,既然“我”(小伙计)作为小说里一个人物出现,他在发挥“观察者、叙述者”的功能的同时,也必然要显示出某种独立的意义。
例如,小说的开头部分,作者为了说明幼年当过酒店小伙计的“我”,为什么会忽然说起20多年前的故事,何以对孔乙己特别有兴趣,用了整整两节的篇幅,反复渲染酒店小伙计生活的“单调”“无聊”,这才自然引出“只有孔己乙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的话头。
除了这类结构性意义之外,小伙计个人命运中的“单调”“无聊”所传达出的“寂寞感”与“压抑感”,也自有独立价值,构成“孔乙己”周围的社会环境和气氛的一个有机部分。
“我”(小伙计)的独立意义更表现在,随着故事的进展,小伙计自身的性格,以及他与孔乙己、酒客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在小说开头部分,“我”确实保持了“旁观者”的客观与冷漠的话,以后,他就逐渐地参与到故事中来,特别是小说写到“我”如何“附和着笑”,当百无聊赖的孔乙己主动与“我”攀谈,以寻求心灵慰藉,“我”先是应付,既而“不耐烦,懒懒的答他”,最后竟“努着嘴走远”时,不能不让人感到,“我”(小伙计)的精神境界、地位都逐渐向麻木、冷酷的“酒客”靠拢,最终不免被“同化”: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精神悲剧。
“我”(小伙计)这种变化在读者欣赏心理上甚至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前所述,叙述者小伙计在小说人物(孔己乙与掌柜以至酒客)的关系上处于旁观者(局外人)的地位,这是与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旁观者(局外人)地位有相近之处的。
这样,读者不仅在阅读之初很容易与叙述者采取同一态度对待(看待)孔乙己,而且,随着叙述过程的进展,当叙述者小伙计也于无意识中参与了对孔乙己的折磨时,在诚实的读者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类似狂人“我也吃过人”的有罪的自省:这样的效果正是作者所追求的。
这样,我们就进一步发现,尽管作者本人并没有作为一个叙述者在小说中直接出现,但是在“我”(小伙计)的叙述中,读者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存在,即叙述学中所说的“隐含作者”的存在。
这就是说,在“我”(小伙计)“看”(叙述)“被看(孔乙己)/看(酒客、掌柜)”的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隐含作者在“看”,不仅冷眼“看”看客(酒客、掌柜)怎样“看”孔乙己,而且冷眼“看”小伙计怎样“看”看客与孔乙己,隐含作者的“看”,构成了对“我”(小伙计)的“看”与“看客”(酒店、掌柜)的“看”的双重嘲讽与否定。
于是,读者终于穿透叙述者“我”(小伙计)冷漠的语调与“看客”们的冷酷的嘲弄,感受到了隐含作者鲁迅对于小说主人公孔乙己(知识者)的悲喜剧命运的同情、焦虑。
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开始,读者也许会较多地认同叙述者(“我”)对孔乙己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旁观态度,但随着叙述的展开,隐含作者(他的眼光、情感)逐渐显现渗透,读者就逐渐与叙述者拉开距离,而靠拢、认同隐含作者,终于从孔乙己的“喜剧”里发现了内在的“悲剧性”,到小说结尾时,叙述者讲到孔乙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时,读者不但不可能如“我”(小伙计)似的“附和着笑”,而且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孔乙己的故事”与“我”(小伙计)的“叙述”,并引起更深远的思索。
——而这,也正是作者的目的(追求)所在。
至此,我们就可以多少领悟到鲁迅在《孔乙己》里选择小伙计作为叙述者的深意。
由这一选择,形成了小说三个层次的“被看/看”结构:先是“孔乙己”与“酒客、掌柜”之间的即小说人物之间“被看/看”;再是“叙述者”(小伙计)与“小说人物”(孔乙己、酒客、掌柜)之间的“被看/看”;最后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被看/看”。
而实际上“读者”在欣赏作品时,又形成了“读者”与“隐含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被看/看”。
在这样的多层结构中,同时展现着“孔乙己”“酒客、掌柜”与“我”(小伙计)的三种不同形态的人生悲喜剧,互相纠结、渗透、影响、撞击,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小说中的人物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就呈现出既是非单一的、多面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
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显示了鲁迅非凡的思想与艺术功力。